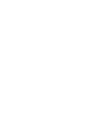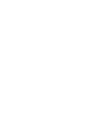我在泰国卖佛牌的那几年 - 第396章:皮滔
我在泰国卖佛牌的那几年 作者:鬼店主
阿赞巴登站在法室中央,举起小玻璃瓶,念诵着经咒。 几分钟后,我们看到那个小瓶里似乎出现了一些淡淡的烟气,在瓶中来回撞击,慢慢地飘着。阿赞巴登用木塞把瓶口封住。盘腿坐在阿赞nangya面前,右手按在她的额头上,左手紧握玻璃瓶,十几分钟后,阿赞nangya忽然张大嘴吸气,但没有呼气。嘴也一直张着。
我们几个人都很紧张,阿赞洪班站在旁边,仔细看着阿赞巴登的施法动作。阿赞巴登张开左手,玻璃瓶里已经没有了那股淡烟,他停止念诵,阿赞nangya缓慢吐气,还发出“啊啊”的声音。
方刚点了点头:“可算救回来。”我们这些人也都松了口气。
阿赞nangya的魂魄被巴登抢救回体内,晚上吃饭时,阿赞巴登给我们讲了魂魄降的原理。那是菲律宾鬼王派的独门降头术。东南亚各国虽然也有些降头师自称能给人施魂魄降,但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真正的魂魄降,让人外表看不出任何伤痕和异常,和熟睡没什么两样,但魂魄已经离体,一般情况下,隔天这个人就完了。围土鸟弟。
老谢问:“阿赞nangya中的这个魂魄降,肯定也是鬼王派徒弟下的了?”
阿赞巴登点点头:“这不用怀疑,但很奇怪,鬼王只有三个徒弟,一个是中国人,姓于,一个马来西亚人。叫登康,还有一个菲律宾人叫皮滔。那个姓于的中国人近几年都没有音信,登康经常在港台活动,菲律宾人皮滔这半年多也很少出来。”
听他说完这番话,我和老谢都有疑惑,但又不好提出口。阿赞巴登似乎看出我们的意思,就说:“鬼王收徒有规矩,必须要亲手给自己的一位家人落死降之后才可以。我因为不同意,所以只和他学了不到三年,对外他并不承认我是他的正式门徒,我也只说是自己修法的降头师。”
我们这才明白过来,我说那人不但给阿赞nangya下了降,还偷走她的拉胡域耶,这又有什么用意?阿赞巴登说域耶是修法者的利器,就像军人喜欢精良的枪支一样。看到就会动心。
方刚问我那人长什么样,我和老谢大概描述了,因为没有太特殊的特征,所以也不太容易描述,无非是皮肤黝黑,中等个头,短发。方刚掏出手机,调出几张照片让我翻看。这些照片有单人的也有多人的,清晰度都比较差,其中有张照片是一名男子在某丛林村庄中,正回头和旁边的人说着什么。我说:“就是他。”
阿赞巴登沉默不语,我们殾能猜出。肯定是鬼王的徒弟了。阿赞巴登说:“他就是皮滔,鬼王的第三个徒弟,菲律宾棉兰老岛人。专落死降,平时还喜欢赌扑克牌,所以有个绰号叫小鬼,没想到他居然到了清莱。”
“会不会是他和阿赞nangya有什么恩怨?”我问,因为我觉得,如果真是蒋姐出钱让皮滔对付我们,他下降的目标也应该是我和老谢,怎么会朝阿赞nangya下手?
方刚说:“看到有阿赞师父在你们身边,他肯定要先铲除威胁,然后才是你们俩。”
出于安全考虑,我在那家酒店又订下了仅剩的三个房间,我们六人分五间住下。我想让方刚和老谢住一间,他死也不肯,说要是让他听着老谢那震天的呼噜声,他宁愿去睡大街。因为清莱地处泰国最北部,住着不少黑衣阿赞和降头师,所以方刚和老谢在泰北都有很多熟人。他俩分别发出消息,托人紧密注意菲律宾鬼王的徒弟皮滔的动向。
两天后,阿赞nangya渐渐恢复清醒,告诉我们那天她正要给那个男人做驱邪法,那男人竟然伸手摸向她左胸,她刚要躲,就觉得神智不清,后面的事就不知道了。
阿赞巴登告诉我们:“魂魄降最有效的方式是对准心脏施降,所用的时间也最短。”
方刚咬着牙:“他妈的,等抓到那个家伙,管你是谁的徒弟,非把那只猪手砍下来不可!”
我正想说话,阿赞洪班却说:“同意!”我们都很意外,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对这种事发言,看来是真生气了。
当晚,有个住在湄猜的朋友给方刚打来电话,称昨晚在湄猜看到皮滔与某黑衣阿赞接触过,但不太确定。为打探消息,方刚提出第二次和我去湄猜看看。老谢和三位阿赞在一起,倒是没人敢惹,但我也嘱咐他千万小心,最好都不要单独出行。
次日与方刚来到湄猜,他的朋友在某条街上开了间佛教用品店,进到店里,那人告诉方刚,昨晚有朋友找他要请一条宾灵,就带他去找当地一位叫阿赞jal的黑衣师父。去的时候,那位阿赞jal正在和另一个男人谈话,他一眼就认出这是鬼王的徒弟皮滔,但怕认错,就和他打了招呼。皮滔似乎很避讳,起身进了里屋。请完牌后,他马上就给方刚打了电话报信。
方刚对我说:“今晚天黑之后,我俩假装要请牌,去摸摸虚实。”
晚上,方刚的朋友带着我俩来到这位阿赞jal师父的家,此人眼圈发黑,头发比鸡窝还乱,家里地上堆着很多各种佛牌,还有装在木盒里的婴胎干尸,屋里还能闻到几分血腥味。我觉得这是个很冒险的行为,如果皮滔把我们三人的照片资料告诉给阿赞jal的话,那就等于自投罗网。但不这样的话,也无法得知这个阿赞jal是否知道我们三人的面貌。
在我俩与阿赞jal见面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留意阿赞jal的眼神,想从中捕捉到哪怕一丝的意外和警觉,但并没发现,这让我松了口气。
方刚对阿赞jal说:“我们俩想给生意场上的对头下个死降,但那人认识一个降头师,好像还很厉害,叫什么阿赞洪班,你能对付吗?钱不是问题。”
阿赞jal想了想:“我自己可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我要是找个帮手,两人联手应该胜算就大多了。”
“哪里找帮手?有像你这么厉害的阿赞师父吗?”我问。可能是有熟人引见,阿赞jal对我们的戒心并不大,他笑着说到时候就有,问我们出多少钱。方刚说只要能让那个人死掉,几十万泰铢都行。阿赞jal眼睛里闪着精光,称最快最要十几天之后,因为他已经收了钱,最近要给三个人落死降,比较麻烦。
方刚问:“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你能不能解决我的难题,万一落降不成怎么办?”
阿赞jal摇摇头:“没有我落不了的死降,除非你没有钱付。”我问他怎么保证有这样的把握,他用手指了指里屋那扇半开着的门,说你们看了那里面的东西就明白。方刚没动地方,我起身去看,见有个人躺在地上,浑身都是污血,手偶尔还在动,似乎是重伤。
我问:“那个人是谁?”阿赞jal称是一位黑衣降头师,前几天被人寻仇,中了刀枪降,身上凭空被砍四十多刀,医院都不收治,正在家里等死。他打听到消息后,就以能解降为由,让那降头师的徒弟把他抬到这里。我没明白这算什么把握,阿赞jal嘿嘿笑着:“那个人最多熬不过明天,用他的头骨制成域耶,效果就好多啦!”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