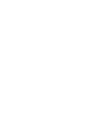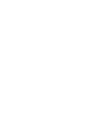租鬼公司 - 第八章 禽兽不如
租鬼公司 作者:侃空
正胸中小鹿乱蹦的艾莉芸被他这一咋唬吓得差点叫出来,不解地问:“想起什么来了?”
“没,没有。”雍博文干笑着说了一句,便又急急忙忙往浴室跑,艾莉芸此刻心里乱糟糟一团也没心思追问。
其实,他是突然间想到在哪里见过那个巨人武士。那巨人武士的模样分明就是那天破阵之后,在阵眼里找到的那个雕像的样子,区别只在于右手里的手头换成了佛珠,个头放大一些。
他早在遭遇之初就怀疑这是布那风水法阵背后之人所为,但回过头来一想,这法阵就是费墨自己布的,费墨既然已经死了,那自然不可能再来寻他晦气,所以便没在这个方向多想,但此刻想到这个问题,便立时意识到这法阵绝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法阵除了聚阴改命之外,还有另一个产物——鬼蛊……这么多年来破茧而出的鬼蛊显然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人间蒸,费鼎新也没有提过这种事情。鬼蛊在普通人看起来或许没什么用处,但这东西对于术法界某些邪门人士用途极大。现在推测起来,或许在这阵法背后还有另一个人或是一帮人在收集这些鬼蛊以作他用。
当初那个雕像被他和刘意送到了法师从业协会做鉴定,但回头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个干净,直到此时才重又想起来,便打算明天一早去协会总部看看鉴定结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弄清敌人是何方人物,还是相当必要的。
现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是相这些乱七八糟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便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
看着雍博文钻进浴室,哗啦啦水声在耳旁响个不停,艾莉芸心越跳越厉害,预想到某些将要生的事情,脸上便烧得厉害,坐在那里眼睛盯着电视,内容却一点也没看进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浴室方向。
二十多分钟之后,浴室里的水声停了下来。艾莉芸也就在同时紧张到了极点,感觉心脏都快蹦到嗓子眼里了,浑身软绵绵的没有半丝力气,整个人都要瘫到沙上了。
又等了二十分钟,雍博文却还没有从浴室里钻出来。
艾莉芸心情稍松,但又有些担心,试探着叫了两声,“小文。”
浴室里却没有半点回应。
这下她可坐不住了,也顾不得避嫌,拐着脚跳到浴室门前,拍着门叫道:“小文,你洗完了没有?”
浴室静悄悄,什么动静都没有,就好像里面根本没有人似的。
艾莉芸咬了咬牙,轻轻一推,门没插应手而开。她探头往里面张望,却见雍博文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浴缸中,双眼紧闭,仿佛失去了知觉。
她心中慌乱,也顾不得其它,连忙跑到浴缸旁边。做为医生,她然后不会大呼小叫,第一件事情却是探手把脉。雍博文脉象平和,她再仔细一看,不禁轻啐了一口,“坏蛋,怎么就这么睡着了?”
当然了,正打算今晚变身禽兽的雍博文本意是不想睡的,但意志抗不过身体需要,那一剑所消耗的精力体力内力法力绝不是短短一段路途所能恢复得了的,只不过当时正在逃命中,他精神高度紧张,才勉强撑到了家里,等到洗澡的时候,诸事皆了,精神一放松,他便不知不觉地沉沉睡去。
看到雍博文没事儿,艾莉芸放下心,轻轻捏了捏他的鼻子,“坏蛋,可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能让人省心啊。”喃喃低语了两句,她忽地心里一动,眼睛转了转,咬着嘴唇,目光就往浴缸下方溜,滑过结实匀称的身体,直到撞上那胯间的黑黑一团,才好像惊弓之鸟般缩了回来。不放心地瞧了瞧雍博文,见他睡得正香,显然没有察觉自己的不轨意图,艾莉芸这才松了口气,回头壮胆一般死死盯着那要害之地瞅了两眼,然后忍不住噗嗤一笑,自语:“果然比小时候长大了好多。”
雍博文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感到极为困惑。
他记得自己明明正在洗澡,怎么一转眼的工夫就跑到这么个地方来了,好在身上衣服都端端正正穿着,要不然还不被人当成露体变态?
眼前是一处长长的回廊,曲折不见头尾,雕梁画栋,精美大气。回廊外的宽广院落中满是盛开的花树,雪白的小花开得正盛,一层层一叠叠,铺满树冠,一地纯白,宛如下了场大雪,微风拂来,满天雪点飞舞,香气四溢,真个如仙境一般。
此地虽好,但终归是来得莫名其妙。
雍博文试探着喊了两嗓子,等了好一会儿,见没人搭理回应,便信步沿着回廊向前走去。不片刻,走出回廊,眼前是一处不大的院落,院落里挤满了灰袍光头的僧人踮着脚尖向前张望,脖子都伸得老长,仿佛许多光头鹅,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一个个屏气凝神,这么多人挤在一处偏却一点声音都没有。从一片光头上方看过去,可见一佛堂飞檐房顶,露着半张匾,上面龙飞凤舞三个大字,任他如何使劲也看不清楚倒底写的是什么。雍博文站着看了会热闹,又试探着叫了两声,但那些和尚却好像聋了一般,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他。他正感莫名其妙之际,忽觉眼前一花,再定神一瞧,却觉自己不知怎么地跑到了人群前方。
和尚群与那佛堂之间隔了大约十步距离,十二个满脸皱纹白胡子老长的黄袍僧人一字排开,站于众和尚与佛堂中央位置,全都闭目凝神,双手合什,在那里喃喃念着佛经。
雍博文不解地搔了搔头,抬眼再看那佛堂上的横匾,却依旧是一团模糊,感觉就跟看片时关键部位打上了马赛克的效果相仿。他盯着瞅了一会儿,终于放弃看清横匾的念头,转过身,围着那十二个老僧转了一圈,用手挨个拍了一遍,又趴在耳边喊一嗓子,但这几个老和尚却跟泥塑木偶一般,连半点反应也没有。他大感没趣,又不能跟这些和尚说话,转头看那些年纪稍轻的灰衣和尚们虽然也都合什作势,但全都神情紧张地盯着面前这僧门半掩的佛堂,便忍不住好奇,走到门前探头往里张望。
佛堂面积不大,约摸有百多平米,正中央供奉着尊佛像,他倒也认得那是大日如来座像,座高跟常人相仿,通体黄灿灿,竟是黄金打造的。
佛着坐着一僧,瞧年纪不过三十上下,白袍光头,眉目隽秀,肤色白里透红,如女子般娇好。他盘坐于蒲团之上,双目微合,双手捏着串乌黑佛珠,膝上放着光闪闪的银制三钴杵,口中喃喃念颂,偏却没有出一点声音。
白袍僧身前立着四个黄袍和尚,俱都面色茫然,紧盯着白袍僧,那神情简直就跟色狼看到光屁股美女一般无二。
雍博文便觉得这白袍僧好眼熟,一时却又想不出在哪里见过,只是见他宝相庄严,竟然不敢走上前去拍拍摸摸,便先走到那左第一个黄袍僧身前。
这黄袍僧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身材高大,足足比雍博文高出一个半脑袋,肤色黝黑,满面虬髯,高鼻环眼,相貌威猛,瞧起来不像是中国人,倒有点像印度人。他左手持着金刚禅杖,右手紧紧捏着佛珠,紧紧抿着嘴唇,似乎努力想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但他那微微前倾的身躯却将紧张心情表露无疑。
雍博文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原本也没想过这阿三和尚会有什么反应,不想这虬髯僧却突然眨了眨眼睛,满面疑惑地左右瞧了瞧。
雍博文吓了一跳,连忙往后退了一步,不想这一步正踩到了左侧第二个黄袍僧的脚上。
这第二个黄袍僧五十出头的样子,颔下三缕长髯柔顺光滑,满面斯文气质,要不穿了僧袍且剃个大光头,那看起来更像是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他左手托着个光溜溜闪亮的木鱼,右手拿槌,虽然站在那里,但目光游移不定,显然是在走神。雍博文这一脚踩上,他便一咧嘴,好险没叫出声,左右瞧瞧,目光没在罪魁祸身上停,却落到了中间那白袍僧身上,脸上涌起一丝愧色,连忙凝神站好。
雍博文站稳了身子,对刚才生的事情不禁大感奇怪,重又走到虬髯僧面前使劲挥手,但这回虬髯僧却半点反应也没有了。他挠了挠头,走到长须僧跟前,对着他的右脚猛踩一下,但那长须僧恍如未觉。
难道刚才只是凑巧?雍博文不禁直犯糊涂,想了想,又走到第三个僧面前。
此僧瞧起来也不过是四十几岁的年纪,但满面风霜,躬腰驼背,满是老茧的双手捧着三藐母驮,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瞅着白袍僧,虽然面无表情,但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敬爱之色。三藐母驮是转经轮一类法器,这东西活象小孩玩的拨浪鼓,由两个用朱砂写着许多梵字的圆形木块叠在一起而成。雍大天师不识此物,还在心里直嘀咕,这老和尚年纪一大把,居然还玩拨浪鼓,难不成修佛修得返老还童不成?
雍博文先挥手再踩脚,驼背僧都没有半点反应,便忍不住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驼背僧立时浑身一颤,整个人仿佛变成了蓄势待的野兽,浑身上下充满了可怕的肃然之气。
雍博文吓得一缩脖子,不敢在他面前停留,两步跑到第四人身前。
此人身材矮小,面容清瘦,虽然也是五十左右岁的年纪,但下巴上却溜溜的没有半根胡须,微躬着身体,手捧着个紫金钵孟,双眼微阖,偶尔可见一丝精光自眼皮缝中射出。
雍博文刚溜到他身前,这矮僧突然面露微笑,双手合什,颂道:““摩诃毗卢遮那!”
这矮僧说的是梵语大日如来,雍博文不懂,听得好糊涂,还以为这不起眼的小个能看到自己,一惊之下便喜出望外,连声道:“你能看到我?太好了!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问得起劲,可那矮僧一语之后,便不再说话,只是保持着微笑,目光直接越过他,落到那白袍僧身后。
也就在同时,那白袍僧缓缓睁开了眼睛,有若实质的目光在房中一扫而过,那四个黄袍僧同时躬身道:“南无阿弥陀佛!”
雍博文没有得到回应,泄气异常,转过头来看那白袍僧,不想一接触那白袍僧的目光,那白袍僧面上虽无表情,但目光之中却满是微笑亲切,还冲着他微一点头,显见得是看到了他。
雍大天师这叫一个激动啊,抢上一步就打算说话,但那白袍僧立刻用目光微一示意,他便立刻明白过来,这是让他稍等一会儿。说也奇怪,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白袍僧,但感觉却说不出的亲近,宛如多年知心的密友一般,什么意思只要一个眼神便可以了解得清清楚楚。他也就不说话了,想了想,站到白袍僧身后,接着瞧热闹。
但其它四个黄袍僧看不到雍博文的存在,自然就以为白袍僧是在冲着矮僧点头微笑,其它三人脸上一时都有些不豫之色。
“空海!”白袍僧低唤一声,那矮僧立刻上前一步,跪伏于其身前,恭声道:“弟子在。”
白袍僧右掌轻覆于矮僧顶门,微阖双目,道:“我的弟子众多,出家、在家众皆有,但都或学一部**,或得一尊一契,无人能兼而贯之。像你这样于短短数月,即以两部秘奥坛仪印契,谓之空前,可称三地菩萨也,当传阿阇梨位。”他声音不响,但这一开口便激得虬髯僧手中禅杖上九环晃撞脆响,威势惊人之极。
其他三个黄袍僧同时宣了一声佛号,全都面无表情。
房外先是起了一片乱哄哄的议论声,但很快平静下去,变成一大声佛号,小院中挤了足有二三百人,此时异口同声,震得屋梁轻颤,但论起威势来,却还是远逊于那白袍僧一人一语。
空海与这白袍僧缘浅,只得跟随八个月,原本准许随侍于前便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从没想过竟能得传其衣钵,一时喜不自胜,声微哽咽,“谢师父。”
白袍僧又道:“我已召画工画胎、金诸曼荼罗,请铸工造佛具,请写经生抄经,让你带回东瀛。你当好好把握此段因缘,将密宗扬光大。”
空海伏身道:“尚请师傅恩赐法号。”
白袍僧微一沉吟道:“可号遍照金刚,你去吧。”
空海伏身于地,施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恭恭敬敬地捧着紫金钵孟倒退出门。
白袍僧又宣虬髯僧沙门辩弘,指他得传胎藏密法,可受禅杖佛珠,赐号荼罗金刚。再宣长须僧惠日,指他得传金刚密法,可受木鱼袈裟,赐号大乐金刚。
把两人打走之后,白袍僧最后道:“珍贺。”
那躬背僧上前跪伏听法谕。
哪知白袍僧不宣法,却轻声问道:“你可是心有不平?”
“是。”躬背僧也不否认,“空海东瀛僧,师父也曾算出东瀛狼子他日必对我中土不利,为何要传他衣钵?弟子自知道行浅薄,不能承师傅衣钵,但惠应、惠则、义操等师兄尽都得传两法,弟子愿替师傅行走唤其归来,以继衣钵。”
白袍僧微微一笑,轻声道:“我诸弟子中,以你入门最晚,平日修行也不出众,你可知我为何选你随侍行前?便是看中你出身穷苦,生性坚忍,且有慧根,可于将来法难之中,将我密宗于中土延传下去,不致断绝。”
珍贺冷汗如雨,将背上衣衫都打得精湿,伏在地上颤声道:“弟子浅薄,难堪此重任,愿请诸师兄同来听训,请师傅详教。”
“大事因缘不可说也……”白袍僧微微一笑,将手掌覆在躬背僧头顶,“我赐你号大日金刚,传你破魔剑印与三藐母驮,统领十二法将,我已留下法谕,等空海等人归国后,便可召示青龙僧众。你须谨记,将来无论如何艰苦,亦须将我法脉传下。”
密宗信奉的是大日如来,赐号大日金刚,这所托之重不言而喻。珍贺诚惶诚恐地领了法谕转身离去。
雍博文对佛教一窍不通,但大致也能看得明白,这是中间这看起来年轻的和尚大限将至,给几个弟子分遗产呢。好不容易等四个黄袍僧都出了门,他就想要开口问个明白,不想那白袍僧轻笑道:“如何?”
雍博文微微一愣,刚要答腔,却听那大日如来座像后有人脆声道:“青龙阿阇梨,你的传法弟子人人有东西拿,那我这护法行者有何好处?”一人随声从黄金座像后转出,却是个年轻女子,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着素白衣裙,乌黑长随意披散,直垂至臀,赤着双足,雪白足踝上各环一串晶莹剔透的珠子,每颗珠子内浮有一个梵字,字周红光缭绕,仿佛烈焰升腾舞动不休。
雍博文努力想要看清这女子长得什么样,但她面目一团模糊,如那横匾一般难认,不禁心里直犯嘀咕,连叫邪门。
白袍僧起身向那女子躬身一礼,却不说话。
白衣女子恼道:“打什么哑谜?你要不说个明白,休想将来我会帮你。”
白袍僧呵呵一笑,“一切诸佛花间出,一切智惠果中生。花间,日后有劳你了。”说完转身冲着雍博文走来。
雍博文还以为他要跟自己说话,摆了张笑脸迎上去,还没等开口,那白袍僧仿佛看把戏似的,围着他转了一圈,随即跌坐到蒲团上,左手拇指弯曲,握入手间,食指直立——而那食指又握住拇指,击于地面,右手曲拳伸食指点着胸口,吟道:“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此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吟罢双目一合,便没了动静。雍博文听不懂这佛谒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白袍僧左手结的那是金刚拳——大日如来的法界定印,但这形象让他猛然间回想起在那算命先生竹签上所见的图像,忍不住指着白袍僧惊叫:“你,你,你不是……”没等他说完,房外响起一片轰然宣佛之声,仿佛平地里打了个霹雳,震得他头一晕,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大地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身子不住地向下坠去。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