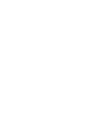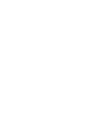关于我哥和我男朋友互换身体这件事(1v2) - 16未尝不是一种中之人 Уūzнāǐщū.ρω
次日,厨房。
“对对,手再往左一点……啊、就是这里,用点力用点力,保持住……都叫你保持住了!”
我坐在流理台边缘,懊恼地推了推陶决,“你行不行啊,再来一次。”
陶决反复深呼吸,几乎要捏碎手里的玻璃杯。
“就一个杯子,从柜子最顶层拿下来放回去拿下来放回去,十五次了,有完没完?还有,用力是用什么力,哪里用力,你不说清楚我怎么知道?你是魔鬼甲方吗?!”
我抱着胳膊摇了摇头,甲方发言一句接一句:“这还得是你自己领会,实在不行就交给身体的肌肉记忆嘛,我看你第一次放上去的发力方式就很好。”
“不是,你到底想让我领会什么啊?”陶决一脸崩溃,“又是‘弹钢琴但要弹得像不会弹钢琴’,又是‘伸懒腰但要伸得像没在伸懒腰’,现在还来这个……陶然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就想折腾我?”
我不置可否,并诚恳道:“拜托了,这真的对我很重要。”
一切的根源当然是两个本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男朋友和我哥——在某种不知名力量的作用下交换了身体,导致我男朋友必须在陌生的地方独自生活,我哥必须假扮十八岁大一新生,兢兢业业替人上课。
而我……
其实本没有我什么事,直到我开始必须以自助的方式搞点黄色,来拯救我看似一片祥和实则一塌糊涂的心理状态。
糟糕的是,由于错过最佳时机,就连搞黄色的难度系数也翻了一番——χfádìáń.cǒм(xfadian.com)
一周多前,我还能抓着床单从梦中醒来,全心投入世俗而浅薄的肉体快乐;现在,我彻底不会湿,看片都能从演员的姿势体态中读出禅意。
这不是我第一次濒临复发。
实际上,最近一次就在去年。当时为了那点救命的多巴胺,钟意频频献身帮我,如同舍身饲虎割肉喂鹰,消耗掉床头柜抽屉里的大半盒安全套,留下许多供我日后取用的回忆素材。
我自知不该总是靠他,毕竟这对他也不公平。更何况他如今人在千里之外,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这一次我只能靠自己。
再加上一点点想象力。
比如说,停电的浴室,交错的呼吸,水花声,皮肤上滚烫而湿润的触感,箍紧后背的力道……
还要再说明白一点吗?
因为正在我哥身体里的我男朋友从外表上怎么看都是我哥,所以我只好用正在我男朋友身体里的我哥代餐我男朋友。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充当工具人的陶决不需要知情,因此我毫无心理负担。
当然,出于对他的保护,我会做得巧妙一些,让他猜不出我的意图,哪怕这会显得像是我在发神经。
——被翻来覆去折腾大半天,陶决身上已经没了那股小心翼翼的别扭劲,现在比起担忧我抑郁复发,他或许更担忧我脑回路有什么大病。
“快快快,一个动作而已,”我不给他时间深想,火上浇油催促道,“真是最后一次,给你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你行不行就在此一举——”
头顶被压了一下。我反射性地闭嘴缩脖子,罪魁祸首便按着我的脑袋借力,投下一片足以将我罩入其中的阴影。
卫衣宽松的领口向一侧滑去,肩线因动作紧绷起来,削瘦的锁骨离我鼻尖不到五毫米。
他没有收手,我不能后退。
上方传来玻璃杯底落在木板上的声音。
“……我让你放旁边的柜子,没让你放我身后这个。”
“所有杯子都在这边,就留一个在那边?你不难受我都难受。”
“噫,强迫症。”
“所以呢,”陶决退开一些,放我早已不堪重负的脖子自由,“够了没?”
“……够了。”
“那就赶紧让开,我要做饭了。”
他撸起袖子去翻冰箱,背影都透着不耐烦。
我哆哆嗦嗦滑下流理台,双脚触地一阵腿软,又做贼似的擦了擦台面。
——————
最近叁次在忙搬家和工作上的事情,感觉一段人生的结束每次都这么猝不及防,总是站都没站稳被就推着往前走,像我经常做的噩梦里因为开得太快从高架桥上冲出去的车。
我不喜欢失控感,但生活的常态好像就是失控。
写这篇文也是,开始只是一个点子,一些大约不太常见的play(?),一种叙述方式上的尝试。但现在剧情慢慢展开,就发现早期设想的一些东西——比如抑郁症,比如性少数者的struggle,再比如现在还没写到的一个主要事件——很难用轻松的、四两拨千斤的形式呈现出来。
想表达的东西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想,这么表述会不会不够谨慎,会不会不够尊重,会不会有美化、娱乐化他人困境的嫌疑,会不会被人出警(纯属瞎担心,糊是最好的保护色)。
当然,我觉得进行这种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创作者的责任——并不是指“自我审查和自我设限是写作的一部分,不爽不要玩”,而是创作本身就等同于一种对自我的审视,也有必要经过一个发现问题、改进问题、输出更加成熟的内容的过程。
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不轻松,甚至有些痛苦的过程。痛苦的蚌和痛苦的沙子不停磨合,直到最后一刻,没有谁能断言这里会产生珍珠。(此处插入一个完全不生硬的求珠珠)
停下来的几天都在重读前十五章,总算把之前怎么改都不通顺的地方理顺了,痛苦中带着点开心,感觉这个刹车踩得很值。
嗯,我又可以继续了。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