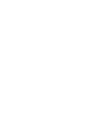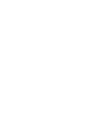齿痕(骨科) - 独白(陈嘉屹)
那天,我一个人又去我们的家坐了会儿。
或许我说错了,那是我后来强加给她的家。
因为她在我们吵架后就毫不犹豫的搬离了这里。
人说失去了才懂得后悔,明白这个道理或许需要时间,或许只是突然看到那个人的照片。
电视柜下面,摆着我们的合照,大学毕业时候,我叫她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水央笑得很开心,就站在我的旁边,头微微偏向我的胸口。
其实我原本不赞成这样的观点,既然很珍惜,又为什么会失去呢。
我描摹着照片里她的轮廓,是几年前了。如今她都蹿了个子,长到我的肩膀。
我忍不住起身踱步她的卧室,这里被她收拾地很干净整洁,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
我坐在床上,触碰着浅色的床单,旁边有几个我从小开始买给她的玩偶,还有她曾经自慰时垫着的软枕头,上面好像仍旧带有一丝馨香。
打开衣柜,低头入目就是她生日那件破了的外套,她没有扔,还迭在这里。
她当时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在这间屋子里和我擦枪走火,我们差点儿做爱。
妹妹应当揉洗过,我嗅到上面淡淡的洗衣液香气。
衣柜底端静静躺着一个礼盒,我亲手摆在这里的,是那条鱼尾裙,别说穿了,她后来连碰都没有碰。
我已经没有任何兴趣订花,矮几上的荷花早就枯败。
我将手指轻移,指尖似乎还能感受到妹妹曾捧着花茎插进花瓶时留下的温度,那种微妙的感觉。
那一刻,我闭住有些微潮的眼,还仍然想保持着一种面不改色,去告诉自己,接受她终于不再愿意回来的事实。
……
当20岁第一次梦见她,她穿的内衣和现在的款式不同。那时候,她的内衣上没有白色的蕾丝边,只是印着红色的胡萝卜和兔耳朵。
她坐在我身上,费力地想吞下我,我本意是想推开的,可梦里的男人竟然可耻地箍住她的腰让她坐下去。
起初我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愤慨,可妹妹似乎无知无觉,她仍然会在周末我回家看电影的时候,用没穿内衣的胸蹭着我的胳膊。
她会用栗子蛋糕上的奶油在盘子里画一只小狗或者小猪,举起来傻乎乎地问我可不可爱。
她会用双面胶去粘贴已经碎裂的瓷盘,弄得歪七八扭,却在某些角度像艺术品。
她会在篮球赛上警惕地看向给我送水的女生,好笑霸道地告诉我,如果交女朋友得等到她30岁。
她很喜欢彩色的玻璃,买了几十个玻璃杯,还送给我好几个最漂亮的,我不得不承认妹妹的眼光很有品味。
她会蹲下喂给流浪小动物火腿肠,我发现她喂流浪狗时喜欢和小狗小猫说话,问人家叫什么。当然,只有汪和喵的回应。喂完后再叮嘱它们过马路一定要看车,然后再挥手告别。
她会拉着我不厌其烦地逛小吃街,坚持不浪费,吃到好吃的就手舞足蹈,那些不爱吃的都可以撑到吃完。
我被学院老师批评上课睡觉,她就塞给我一大把剥好的开心果,说吃了就给我表演会变开心的魔术。
她真的会凭空变出一朵玫瑰花递给我,我全然不知道她竟然学过。
她学东西的能力一向很强,学习也很刻苦,常常到深夜还在房间里叽里呱啦背历史。
她也会紧紧抱着我让我哄睡,我小时候给她讲故事,她大了就让我讲鬼故事,我不会,她就开始表演鬼伸出舌头吓唬我。
该怎么形容我的妹妹呢,本是那么灵动鲜活的灵魂,从初来陈家的不安局促到后来的依赖与活泼。
也是,她一直很勇敢,是我全然没有想象过的一种灵魂。
我曾经可耻地认为她和我一样流着肮脏的血。
可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爱上她从不是巧合,她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
我出国的时候,她哭得梨花带雨,她也以为,我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
我也很心疼,我知道兄妹之间的羁绊本来就拧不清。我只想让自己暂时缓缓,不要因为日日相对就再做那些关于她的春梦。
出国的机会送过来,我没有不接受的选择。
在国外的日子平静且充实,我的学业压力很大,有时候给水央发消息后就累得睡着了。
她回复后见我迟迟没有回应,便越来越懒得回我消息。
留学其实有时会觉得无聊,那样的日子里会让人们想自寻欢乐。我经常托烟贩子给我带国内那种几十块的平价烟,那股味道令我出奇地上瘾。
学校里曾经加入的滑雪俱乐部有次办了个小范围的私人聚会,有师弟开玩笑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我喝两口酒,摆摆手拒绝这些不正经的暗示。
习惯的拒绝并不难,但看着别人出双入对,有时也会觉得我在国外真的挺孤独,我想她时会抽烟抽得越来越凶,有时候甚至一天两盒。
……
有一天,我在算法科学院做实验,间隙的时候,师兄过来和我搭话,说学校的绿化做得越来越不错了,又问我毕业后的打算。
我的目光落在窗外的绿树上,校园里的伐木工人正在锯着它伸到道路上的枝干。
那树苗我是看着长大的,在这里做实验的每一天,它渐渐发了芽,长出叶子。
透过防辐射眼镜,我看着日光悠悠渗进树叶落在地面。
它总是那么充满活力,汲取一点阳光就是它不竭成长的动力源泉。
我为它那股不顾一切的破土冲劲感到惊讶,就像初生的牛犊,无畏无惧。
然而,太阳的炽热光芒并不会因为这份勇气而变得柔和,树叶根的鲁莽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树一定很痛吧。”一位拿着仪器的意大利师妹用英文有些感伤地说。
我当时难以理解,难道把枝干锯了不是最好的选择吗?树会继续长得更好,道路也会更宽敞。
我这种不太以情感作为价值估量的人,在当时,很难想象人会做出一些疯狂错误的事。
但有时人就是难以预料地打脸,比如我后来回国后,真的睡了自己的亲妹妹。
两次,都是因为看到她喝酒,我变得性欲上头。我本来很讨厌酒气,因为我们父亲就爱喝酒,经常做些肮脏的事情。
他喝醉了,把我的娜莉踢死,那是我此生唯二无力的时刻之一,我没有能力保护它。
妹妹喝醉了总爱撩拨我,却叫我都怜爱地无法拒绝。
在水央身上,我重新体会到了这种完全的倾受保护欲的感觉,我必须把她笼罩在我的羽翼下。
她在房间吃我的手指,发现我在用她的衣服自慰,甚至在车厢里含我,我脸上总表现出被冒犯的不悦,但呼吸却一点点地变重。
人的身体很诚实,我总这样想,也这样慢慢劝自己。
我原本觉得只是妹妹贪玩儿,她那么小,被我管着护着有一些别样的情愫也正常。
但为何我和她,总是难以维持哪怕短暂的一段和谐关系,在她生日的时候,我们又因为一些事情吵架。
当时,我仍旧不觉得我那是她嘴里的掌控欲在作祟。
我只是不想她出去就受伤,不想她交那些朋友让自己身陷陷阱,这些有错吗?
可我们就是在每一次她被我训完,在唇齿相依的瞬间就忘却那些龃龉。
这种矛盾感让我感到难以言说的苦楚。妹妹很小,行事冲动,只有在我可控的范围内,我都尝试理解。
但为何连我自己也会做出令自己困惑的行为,亲她时明明她也在动情,可在每一次交谈过后,我都察觉到了她的变化。
我觉得监控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导火索,我也无法替自己辩驳什么,因为我在装监控的时候还坚持认为,这其实没有对她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每逢我出国,妹妹都太冷淡了。我只是让自己在想她的时候可以不要再用烟和酒来代替。
可这些都太荒谬了,事情越来越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我被她煽动情绪,一次又一次让我吃那些她周围人的醋,违背我想要她好的心。
最终我不再掩饰,看她自慰,干她的时候,身体里逐渐渗出掌控她的气味。
说实话,在不久之前,我对会发展成这样的局面完全没有预料。
爱一个人会让自己变得不像自己,我时常觉得心在酸麻。生气起来仿佛有另一个灵魂开始掌控我。
我想水央没有变,是我变了,于是把她推远了。
那段时间,她总是在性事显得很热情。结束后窝进我的怀里,我们之间的和颜悦色变得很多,她也不再顶撞我。
我有时在床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看着身边沉默不语的妹妹,她的脸显得比从前要苍白。
我们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爆发无法圆和的争吵。
黑暗里,所有隐晦的情绪被遮掩,只留下在情绪上头的情况下,对彼此最恶意的攻击。
她哭着说完她心里的委屈,冲我告别说要去宜南的时候很平静,笑起来嘴角弯成一个恰到好处的弧线。
我后知后觉明白,是她过去在兼容我。
我知道她妈妈的家就在宜南,我没有办法代替她生命中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顿时觉得,她可能不再回来了。
人的意识会蔓延,会在最坏的场景想最坏的结果。那种恐惧感席卷我的全身,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她要走了,就是等于不爱我,等于过去的种种都是假的。
她隔日道别的声音又很轻柔。
“哥,我回家了,你少抽点烟。”
她还是叫我哥哥,说她要走了,说我们再冷静冷静,向从前一样嘱咐我。
夏日凉夜微风,她离开时的身影让我想起了那些悬挂在她喜欢的精品店旋转门上的玻璃风铃。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清脆而悠扬的叮咚声。
我可以用任何脆弱易逝的东西来比喻她,树苗,蝴蝶,小白狗,金鱼……
我给她打造保护伞,在她看来却是伐木工,茧壳,狗链和鱼缸。
我可笑的幻想着这样就不会让她受到伤害。
她却说我的过度守护让她碰得遍体鳞伤。
……
那天在科学院,我冲师兄道: 我会选择回国。
我害怕我养护的树苗会受到伤害,于是开始矫枉过正。
明明她可以不要撞的,只要她愿意用心留在我身边,我想我会让她出去看看天空。
是的,在最后的最后,我终于彻底明白。
用一切狭隘的比喻形容我对她的爱的话,是占有欲为上风,其次是她被我压着操她的感觉,最后才是她的自由与想法。
在她指责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的时候,我在后来失去她的每一个夜晚,很平静的承认了这一点。
受性格影响,我拼命的开始反思,给自己作出很多应对措施。
我想,我可以用很多手段逼迫她,让她改变志愿。
可她手里只有“卒”,大“军”压境,还未照面都知道会输,她还是下了。
于是,我又不舍地收回了棋子。
是啊,妹妹原本是那么鲜活灵动的人,被我养得好好的,怎么变了。那是后来我做错了,让她有了枯萎的趋势,我又怎么舍得一错再错。
……
她上大学不到半年,我也提前毕业,回到学校参加典礼,办理离校手续。
那天是最后览过校园,我觉得图书馆的穹顶格外高,绚丽的彩色玻璃从空旷幽暗处倾泻下来,莲花交错的图案很圣雅,让厅内光线斑驳陆离。
我眼前渐渐模糊,她那么喜欢彩色和荷花,会不会喜欢这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带她来看过我的学校。
师兄正在拍照,看到我,走过来跟我聊起学校的趣事。
他说起科学院门口的那一排树被移栽了。
那时的澳洲已经快春天,到处是芬芳的花香和温暖。
我却感觉手脚一片冰凉,烟瘾又犯了。
月光在天际缓缓沉落,海浪在沙滩轻轻碎裂,灰泥从石墙上脱落,青绿的常春藤掩盖了其后的荒芜;虽然看不见,但始终感受得到残破的气息。
她还叫我哥哥,在微信我们还会聊天,我一次次飞去宜南找她,她仍会邀请我去她学校附近的西北菜馆吃大盘鸡和嫩豆腐牛肉,满口辣椒和我吐槽学校的生活。
兄妹的羁绊果然永远断不了,吵完架放完狠话还得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可一切我所设想的美好,都已无法回到最初的起点。
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一天仍然回到我的怀抱。
我想,我只会轻轻拥住她,不会再使那么大的力气。
然后去告诉过去的我,稍微等等那个不好的自己,长得更加成熟克制再去爱她吧。
哦,忘了提,我此生还有另一个无力的时刻。
就是她终于飞离我的身边。
……
最近宝宝们有给我对情节的设定有一些讨论和建议,微博甚至也有推文在讨论文笔和情节问题。首先我真的很感谢大家愿意一直看到这里,证明这个我一开始很不抱希望像是练笔的故事竟然被大家接受和理解。
这也说明水央和陈嘉屹的情节发展确实出了一些问题,我全部接受并且在全文完结后会回来继续修文。
我是第一次写长篇,有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确实很苦恼,每天一遍遍看本来弄好的大纲,很痛苦地发现两个主人公好像开始有了自我的灵魂,脱离我的笔下。
我不会找任何借口,这就是我处理上的生涩和失误,导致情节突兀产生,很不好意思,也经常红温。
谢谢大家给我提建议鼓励,让我也可以不断地锻炼成长,因为大家评论声音很多,我就在这里统一表达感谢。
下文不会虐,但也不太长了,我不成熟的故事却滋养了两个会成长的主人公,希望他们可以越来越好。
我也会加油在写文的路上。
承蒙不弃。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