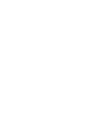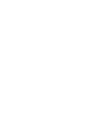和珅 - 34、福康安的探病之旅
索绰罗.英良有听到传召的那刻便心生不妙,不过,他尚存一丝侥幸,或许善保只是走投无路,胡攀乱咬,垂死挣扎罢了。
他椅子还没坐招呼,听到花大咬出大管家的时候已知要坏事,只是人自认做事严密,只凭花大一个贱民的一面之词想咬死他一部尚书,那是痴人说梦。不料善保狠毒致此,不顾脸面,翻出前事,一顶怨望的帽子扣到索绰罗家的头上;再巧言令色,随随便便的多了个失德无行的罪名儿;最后把持会试,毒害举人更是严严实实的铁证如山。
索绰罗.英良本来年纪就不小了,一生气就哆嗦,话都说不上来。善保却是口舌伶俐,声泪俱下,唱作俱佳,最后善保痛心疾首之态难以形容,一捂胸口,呕出一口心头血,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阿玛”,就此背过气去。
钮祜禄.君保也不顾君前失仪,扑过去抱着侄子,捶胸痛哭。
一时步军衙门愁云惨淡,哭声震天。
索绰罗.英良也想吐血晕过去,可善保先行一步,他再晕,就是东施效颦……他就这么哆嗦着,等着乾隆宣判。
善保一直晕到回了家,两个御医在他身上捣弄了一番,才渐渐醒来。这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下子睁开眼,善保先是眉尖儿微蹙,就听一人低声急呼,“醒了。”
一只手按在他的脉象上,善保手指尖儿动了动,听到福保担忧的声音,“哥,哥?”
“老大人,善保是怎么回事,这么久怎么还没醒?”君保焦急的问。
太医摸着善保的脉象,一脸为难,“公子秉性虚弱,身上带了伤,郁结五内,一时激愤,怒火攻心,才会昏迷。”
善保绞着眉毛,睫毛颤了又颤,眼睛艰难万分的睁开一道小缝……张张嘴,说不出话,要死不活的模样。
福保捂着嘴吧嗒吧嗒的掉泪,握住他哥的手,抽咽道,“哥,你可醒了。吓死我了。”
善保偷偷的挠了挠弟弟的手心儿,快别哭了,你哥是装的。福保却意会错了,伏在床上,嚎着嗓子大哭起来,边哭边怀念他过逝的阿玛。
不说别人,君保的一颗老心都要碎了。一屋子人红了眼圈儿,俩太医虽然是被乾隆十万火急收买人心的调来给善保看病的,也听了一耳朵钮祜禄家的惨事,叹一口气,劝道,“二公子,令兄无甚大碍,这已经醒了。容老夫开个方子,服下去过几日就可痊愈了。”
董鄂氏拈着帕子给福保擦眼泪,哄他坐好。
俩太医商量了会儿,斟酌了一张药方子出来,又叮嘱病人的饮食事宜,客客气气的告辞。君保送至仪门方回转去看善保。
善保已经睁开眼,咳了几声,红雁倒了茶,董鄂氏接过喂善保喝了两口。
善保感激的看向董鄂氏,重又闭上眼睛。
董鄂氏对几个小的轻声道,“容你们大哥歇歇,雪儿,带你弟弟们去我院里说话儿。”
待一时君保回来,董鄂氏拉了他去外间说话儿,低声道,“我瞧着善保这是伤了神,我守他会儿,瞧他睡熟了再过去。孩子们在那院儿呢,你去劝劝福保,别吓着他。”
君保心里是有疑虑的,这几日虽说在牢里,善保却是吃得好睡得饱,这说吐血就吐血,说晕菜就晕菜,说虚弱就虚弱……不过,因皇上赏了御医下来,善保“虚弱”些也是好的,君保话在肚子里也没多说,挑帘子看了善保一眼,才走了。
福康安走他大哥的后门儿,也跟着沾光听了一回御审的案子,心里又酸又沉,总有些内疚。
按说也怪不得他,索绰罗家这样人家的女儿,简直是白虎星下凡,谁敢娶啊!
他,他能不跟皇上说么?
那女的也是,落选就落选呗,难道落选就都不活了?人家别人活得好好儿的,偏你就受不住去自尽!
害得,害得善保背了黑锅。
遭了这番大难。
福康安没什么精神,福灵安脸色也不好,那个阖该千刀万剐的花大是他步兵衙门的官兵……
富察夫人见哥儿俩一道回来,面儿上带着倦意,忙道,“可是累着了?”
兄弟二人先请安,富察夫人摆手让他们坐了,又命丫头端了果子点心给他们吃,福康安道,“额娘,没事,就是有些乏。今儿善保的案子过堂,听着叫人心里难受。对了,额娘,让丫头们收拾些补品,明儿我瞧瞧善保去。”福康安道。
富察夫人忙问,“到底是怎么着了?老大,是你们衙门审的吧?”看向福灵安。
福灵安虽不是富察夫人亲生,他生母早逝,自幼也是养在嫡母身边儿,感情融洽,不然也不会娶了郡主,这里多有嫡母帮衬。福灵安叹道,“额娘,别提了,万岁爷都去了。说起来也是善保家倒霉,要不说娶妻娶贤呢,老话断不会错的。他是冤枉的,害他之人就是他继母的阿玛,吏部尚书索绰罗大人。”
“我的天哪,两家也是亲戚呢。”富察夫人唏嘘不已,“这也忒作孽了。为了什么啊?总得有个缘故。”
福灵安瞧了弟弟一眼,生怕母亲多心自责,还是瞒了下来,“还不是因着先前善保继母做的那些没脸的事儿,不说反省,倒恨上了善保,摆了个乌龙阵,幸而万岁爷圣明,才不使奸人得逞,还善保公道。”笑道,“福康安说的很是,善保挨了板子又在牢里呆了这几日,身子怕是撑不住了,福康安过去瞧瞧,也是应当的。”
“善恶到头终有报。”
……
兄弟二人自母亲那儿出来,很默契的去了小书房中,福灵安还是问了福康安一句,“善保这官司透着诡异,那个杂耍艺人,他是如何知道的?还有,索绰罗大人身上的熏香,就算是他那胭脂铺子制出来的,铺子里熏香多了,怎么他就能认出是哪一种?你去他家打听打听。”
“我也正想问他呢。”福康安明白哥哥的意思,这件事,正着说得通,索绰罗.英良也认了罪。可反着来想,更让人心里发寒。莫不是计中计?
福康安摇了摇头,“进士三年才一回呢。”谁会浪费这个机会?不过如今善保也不比考中进士差,还扳到了一部尚书。心绪一时万千繁杂,如乱麻一般,理不出个头绪。
福康安低声道,“他才几岁,照大哥说的,岂不是妖怪了。就是他叔叔,回京不过这几年,索绰家是何等家世,岂是他们能算计的?应是赶了个巧。”
“我也这样想。善保虽有几分聪慧,应该不至于此。”福灵安喟叹,“英良做了一辈子官,临了竟栽在善保手里。”
“大哥,你瞧万岁爷会怎么判呢?”
福灵安拿起书案上一方紫玉麒麟镇纸,“不好说。哼,善保虽是苦主,却失于厚道了。”
福康安撇嘴,不以为然,“他再厚道下去就要没命了,厚道!”很有几分气愤。
福灵安却似未闻,微勾了唇角,眼睛却在镇纸上流连,“原本,他已是拿到了英良陷害他的证据。这已经够英良喝一壶了。接着,他又将两家那点子渊源抖了出来,一个怨望,一个失德,光这两条大罪,英良死不足惜……唉,不知道他家的爵位能不能保住呢。说起来,他家三儿媳还是表姨母的女儿,咱家的远房表妹,怕阿玛又要忙了。”
福康安吃过早饭就去了钮祜禄家。
善保瞧见他虽然还是爱搭不理,不过,这两日福康安尽是做小低伏了,如今善保大仇得报,心情也好,倒没说什么,依旧在床上趴着。
“善保,好些没?”福康安这是吵架后头一遭来善保家,一眼就瞧见当日善保拿回的相框,正摆在床头几上,不由愣了。
善保一声冷笑,福康安回神,轻声道,“那天是我不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鬼上身了,只想着你给我一个人画才好呢,一时就赌气说了些伤你的话。善保,我们和好吧。”说着就去拉善保的手。
善保撅着嘴,黑宝石一样的眼珠子打量着福康安,刁钻的说,“这么容易原谅你,你不得以为我好欺负,以后有事没事的欺负我,反正我好哄,啊?”
福康安给他这种刁话气笑了,屁股坐床前的椅子里挪到床边儿,“这几天你可没少刺儿我,善保,你向来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就原谅我这回吧?”还是得小小拍一记善保的马屁。
善保眉眼弯弯的一笑,也不想再纠结于以前的事。
福康安知道善保喜欢吃水果,带了一篮子红彤彤的草莓来,善保惊喜的问,“这个时节怎么就有草莓了?”
“是宫里赏的,我单给你留出来的。”福康安笑。
灵雀搬了个细腰梅花凳来,红雁将洗好的草莓连同两杯香茶两碟细点心一并放好,笑道,“这草莓虽鲜,到底有些凉,大爷悠着些,别吃得太多,晌午还得吃饭呢。”
“越发絮叨了。”善保笑嗔,“外头若还有,给二婶送些去,你们自己也洗些吃。”
“奴婢已经留出来了,这儿就给太太送去。”
善保将枕头竖起来,靠坐在床头,福康安担忧的问,“你屁股没事了?不是挨板子了吗?”
“怎么不疼?忍着呗。男子汉大丈夫,能为这一点儿疼就哭天抢地不成?”善保振振有词,拿了颗草莓咬一口说,“我原本想着不是福大哥坐镇的衙门么,一板子没少挨,差点儿要了命。”
福康安道,“谁让你去叩阍的,别说你,就是天王老子去敲登闻鼓,也得先挨板子。你命好,圣上慈悲,如今减到四十板子。你要是早生几年,在圣祖年间,得挨八十板子。”
善保笑,拿帕子擦手,“我就这么一说,其实多亏福大哥照应,那牢里起码干净。你回去替我跟你大哥说声谢啊。说起来,还得感谢丰绅济德、丰绅济伦他们呢?”
“可不是,他们每天去牢里看你呢?”福康安嘴里开始泛酸,善保笑着拍他一巴掌,“你想什么呢。不是他们,我还想不起那个花大的身份呢。你忘了你过生日那天邀我去你家,我陪他们看杂耍。”
福康安张张嘴,问,“花大就是变戏法的那个?”
“是啊。”
“我记得当时那些人都勾了脸,你怎么认出来的?”
善保低头从碟子里挑草莓,无所谓的说,“丰绅济德一直问我那变戏法的诀窍,我多瞧了几眼就记下来了。你不懂画画,可能不清楚,虽然那天他勾了脸,不过有许多跟常人不同的地方。比如,他脖子上一颗黄豆大小的黑痔,两只耳朵也不一样,左耳是我们常说的招风耳,右耳就比较服帖。还有脸形,眼睛,这些都不会变的。还有他在台上谢赏时的口音,都能听得出来。我也是想了许久才想起曾见过他。”
“那你说的查他们戏班子的事,有鼻子有眼的……”
“你怎么不动个脑子,那是我吓唬他呢。就这么两天,我在哪儿去查他的根底哪?”善保拈着草莓吃了一个又一个,这年头儿,无污染,草莓格外甜,都不用醮白糖,善保开心,也乐意为福康安解惑,“你想想,会试一共九天,到第七天,花大才诬我作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人胆子小,要是个胆大的,不会等到第七天动手。他既胆子小,定是怕死。我一吓,他就招了。”
“善保,你虽不大出门,可这见过的人不知有也不少,怎么就能想到是花大,你那天不过是在戏台上匆匆看了一眼。”
善保叹道,“你知道街上算命的为何喜欢看手像么?”抓住福康安的手握两下,摸摸他掌手的厚茧道,“一摸就能知道你是习武的,掌心都磨出茧子来,手也硬。当日,花大推我出贡院的时候,我拽住他的手,就想这人的手真软,不像官兵的手。或者不像平常男人的手。还有他说话的腔调,仔细想想,就记起来了。”
“可你既然早知道那张小抄上有索绰罗.英良的熏香,怎么没早说呢。”
善保先看了看门帘,高声道,“红雁,你们出去玩儿吧,这屋里不要留人了。”
听到侍女出去,善保方正色道,“我只对你讲,你可别说出去。”
“你放心。”
“没有什么熏香能带到纸上停留长达十天之久的,”善保倚着床看着福康安,端起一盏茶,轻声道,“那张小抄上的香并不是冷梅香,只是松烟古墨的墨香罢了,我在考场当日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余先生偶尔会用松烟墨,与普通墨不同的是,墨里散发一种冷香。这种香多是制墨时加的冰片麝香或是什么珍贵的香料。”
“索绰罗.英良是个很谨慎的人,小心的过了头,做事并不干脆。当初索绰罗氏夺了我家家业时,以索绰罗.英良的本事,无声无息解决我同福保并不是难事,他却留了我们一条小命。还有,他恨我至此,却要等到我会试时才出手,可见已经准备的天衣无缝。该清理的人已经清理了,该打发的也打发了。这个局若是做成,不仅能解决我,连我叔叔也一锅端了。他肯定很得意。像余先生,每次写一副好的斗方,就会拿出来反复的看。索绰罗.英良眼看就要大仇得报,岂能不更加小心。太过小心的人是不放心别人的,节骨眼上,更不能出现纰漏,这支笔、这张小抄是要做为证据留在考场的,他怎能不反复检查。”善保半眯着眼睛,摸了摸手里的茶盏,“他到步军衙门走过我身边时,我留意到他身上的熏香是铺子里年前所制,灵机一动,就想出了这个主意。”
“只是索绰罗.英良能位居一品尚书,可不是花大这等没见过世面的艺人,不是好诈的。所以我先把索绰罗氏的事情说了出来,再有选秀不成反自尽,这就是对朝廷的怨望。圣上自然会动怒,而索绰罗.英良也恼羞成怒,恨我欲死,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平常的理智。我才会把熏香的事拿出来说,族中丑事尽为人知,他声望全无,再有这桩案子,矛头也指向他。这世上哪里真有天衣无缝的局呢?他心里有鬼,此刻已是惊弓之鸟,随便什么响动都能要他的命。何况我将熏香之事说得信誓旦旦,你这旁观看戏的都信了,何况他这当局者呢?”
福康安讪讪一笑,“我是担心你。索绰罗家到底是满洲大姓,他家长房袭公爵、伯爵的也不少,可别让他回过神,再翻状。”
“他是不会翻状的,光索绰罗氏做的那些事,已经是门风不正、教女无方、为人唾弃,他心里明白。他认不认罪,这案子始终是指向索绰罗家,刑部再审,怕要把他的御史儿子赔进去。圣心已失,他是死定了,如今暂且苟活牢中,不过是为了保住家中老小罢。”善保淡淡地,无悲无喜的模样。
“说起来,还有不少疑点,会试都是礼部在安排,那个花大如何能在贡院大门口检查考篮,还就偏巧在你的考格外头站岗,这里头定有不少猫腻。”福康安如今对善保的智慧大加赞叹,他都能想到,不信善保想不到。
哪知善保微微一笑,“如此结案已是大善。这案子事关今科春闱,虽然涉及一部尚书,不过是我们两家恩怨。难道还要株连到礼部上头?你当我不知道礼部尚书他他拉.林卓,替索绰罗.英良遮掩么?说起来他们两家还是姻亲。只是牵扯到礼部,举子们难免质疑春闱是否公正了。日后榜单一出,少不得许多闲言碎语,于朝廷脸面也不好看。我就没提。”
“你如此识大体,只是可惜你这科,还要再等三年。”福康安很为善保惋惜。
善保喝了两口茶说,“这也是天意罢,我想着等伤好了,出去各地转转,开阔眼界,长长见识。”
福康安大惊,“你要出远门?”
“嗯。这科已是错过了,我现在年纪小,补不了差事,趁现在有时间,各地转转。去年来我家的随园先生是江浙人,对我说起过苏杭美景,吴侬软语,江浙风情,心向往之。”善保脸上一派神往之色。
福康安却是不乐意,恨不能劝善保息去此念,道,“没什么好看的,也就是些山山水水,人物风景,寻常的很。长途跋涉的,去那么老远,咱们见面都不容易。我,我明年大婚,你难道不来喝杯喜酒?”
“你还有脸跟我说大婚,你说说,谁老婆子嘴把索绰罗家的事捅出去的?”善保捶了福康安肩膀一拳。
福康安尴尬的笑,“善保,我那也是没法子了。原先大姐姐帮我打听了,说皇上要把索绰罗家的孙女指给我,吓得我连做两天恶梦。那种白虎星,哪个敢娶?这推也得找个可信理由不是……”
“你得罪人,叫我背黑锅,”善保奚落着,“还有脸在我跟前儿摆福三爷的谱儿。”
“善保,我都跟你赔不是了,你还要记多久哪。”
“记多久?我向来过目不忘,何况这种叫我气了好几天的事呢,说不好就得记一辈子呢。”
福康安听这话,知道善保已经消了气,不过是讨个口头便宜,眉开眼笑的附和,“记着吧,能让善保记一辈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拿了个草莓递到善保唇边,“呐,吃吧。我伺候你善保大爷一回。”
善保张嘴就吃了,唇角残留一丝果汁红渍,福康安指着笑,“瞧你,还不擦了去。”
善保舌尖儿露出一点舔了舔,问福康安,“还有没?”
福康安自袖中取出帕子,一手拖了善保的下巴,一手给他细细擦干净,“懒死了,拿个帕子能累着你。”嘴里念叨着,指尖儿却在善保的脸上流连,细如脂玉。他房中两个侍妾,模样性情也是上上等,跟善保一比……
“擦好没?再给我拿一颗。”
福康安手一僵,拈一颗塞善保嘴里,“你倒是会使唤人。”眼睛却移不开视线,这几年,善保渐渐长大,去了幼时的稚气,愈发俊美了。又兼他用功念书,气质温润,眼界开阔,自有一股与众不同的味道。
福康安下晌午得去当值,早早与善保告辞,一整日的心不在焉。
侍卫相当轻省,每日守两个时辰大门,还是做六日歇六日。小喜子偷瞧福康安的脸色,也不像累着的模样,便未多嘴。
回房后,两个侍妾迎上前服侍福康安换了家常衣裳,这两人,乃宫中所赐,一个温柔可亲,一个娇俏甜美,平时福康安也乐得与她们说笑,今儿却失了兴致。斜倚在榻上,只是慢慢喝着参茶。
“爷可是乏了,奴婢给您揉揉可好?”宁儿温温柔柔的坐在榻旁,水漾的眸子荡漾着万千欲语还休的柔情。
福康安盯着宁儿温婉的脸蛋儿,伸出手去,扣住宁儿小巧的下巴,细细摩挲着,宁儿温顺的低垂着头,脸儿却渐渐红了。
“这是用的什么胭脂?”福康安对着一张修饰的精致如画的脸,忽然间意兴阑珊,善保什么都不用,脸上从来都是干干净净。
宁儿细声细气的说,“是老太太赏奴婢的,说是大爷拿回来的。奴婢和可儿妹妹一人一套,比以往奴婢用的都好呢。”
可儿倚着门框笑,“爷,胭脂有什么稀奇的,奴婢听说现在城里有一家卖香料的铺子,一种香料只卖一人……嗯,那香佩在身上,香气弥久不散,听说现在千金难求呢。”
福康安笑看她,“怎么站得那么远说话?”
“奴婢怕扰了爷和姐姐的兴致。”说着自己先捏着帕子笑了,摇摇摆摆的走至福康安跟前儿,福了一福,才笑嬉嬉的盈盈坐下,又似黄莺出谷似的问,“爷,奴婢和姐姐听了半天的故事,说的就是前儿举人蒙冤叩阍的事儿,真跟以前听的话本一样。”
福康安惊奇,“哟,这都传到内宅来了。”
可儿明眸得意的一转,“瞧爷说的。奴婢们虽然大门儿不出、二门儿不迈。可这样惊天动地万岁爷御审的大案子,除了四九城的瞎子聋子,如今还有哪个不知道的。”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